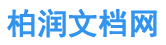王文胜
在中国现代历史上,“日本鬼子来了”是中国人尤其是南京人刻骨铭心的创伤记忆。身为南京人的叶兆言,他的许多小说文本都是对抗日战争创伤记忆的书写,从最早的《追月楼》 《日本鬼子来了》,到《古岭事件及其他》 《一九三七年的爱情》,再到新世纪之后创作的《一号命令》 《很久以来》和《刻骨铭心》,均书写“大时代中”的伤感的“小故事”。他说:“作为小说家,我看不太清楚那种被历史学家称为历史的历史。我看到的只是一些零零碎碎的片段,一些大时代中的伤感的没出息的小故事。”①叶兆言的这些小说被称为新历史主义小说。新历史主义者接受了福柯、怀特等人对历史和文学同质性的思考,“将文学和历史叙述交还给它们同属的文化网络”②。20 世纪后期,福柯、怀特对历史和文学同质性的思考对文学、历史学界的影响巨大,历史研究的“记忆转向”是最直接的表现,“记忆因素对现代历史研究的介入,尤其是‘集体记忆’概念的提出和言说,实实在在地令传统意义上似乎只为专家学者所拥有的‘历史’变成了当今世界与我们每个个体都息息相关的‘历史’。除了著作、文献、档案、历史学家,我们还可以从小说、影视、传记、每个日常化的个体来接触历史、感受历史,历史也变得‘日常化’了”③。这些研究成果开阔了文学批评的学术视野,在对新历史主义小说进行文学批评时亦需要“记忆转向”。本文尝试从叶兆言抗日叙事中的几个关键词入手来研究他是如何具体运用象征性修辞、互文、拼贴、跨文本等方法营造了抗日战争的文化记忆空间,同时指出它们不仅承载了民族的创伤性情感,也在民族认同、民族精神构建方面有重要的价值。
《日本鬼子来了》是叶兆言早期的一部短篇小说,小说的命名就是一次成功的文化记忆编码,作者不仅透过“日本鬼子”这个在中国近现代历史过程中生成的专有词汇打开了一段刻骨铭心的国族记忆,“日本鬼子来了”也成为创伤历史的转喻,我们借鉴汉语史研究者对“鬼子”的释义考辨能更为清晰地理解“日本鬼子”的文化记忆建构。
《辞海》以《世说新语·方正》为例,将“鬼子”解释为“骂人的话”。学者考证进一步指出了“鬼子”在中国文献中被释义为“詈骂”的因素在于:“(1)由于词缀‘子’有表小称的含义,故‘鬼子’比‘鬼’被赋予更多的轻蔑色彩(2)受层级心理习惯的影响,鬼丑陋,鬼子更丑陋,鬼可恶,鬼子更可恶,鬼无能,鬼子更无能。”④
根据汉语史学者曹翔的考证,清朝初期,国人以“天朝”自居, 称外国人为 “鬼子”,当是自大心理膨胀到极致的表现,是对外国人的蔑称,当今《汉语大词典》对“鬼子”的释义保留了这一义项。“鸦片战争以后,‘鬼子’一词多数情况下是与外来侵略者联系在一起,是与侵略者的残忍、恐怖联系在一起。‘鬼子’一词遂由蔑称变成了畏称。”⑤
史学界的学者也注意到了“鬼子”的词义变化与中外关系以及民族认同情感变化之间的关系⑥,认为“七七事变”之后,“‘鬼子’内涵更为具体,凶残的词意进一步前置,类似于作恶多端的魔鬼。日本士兵水野靖夫被俘后,对于中国人怒斥他们为‘东洋鬼子’很是沮丧:‘什么叫‘鬼子’?我们是日本兵呀!……怎么能把我们叫魔鬼的儿子呢?’此亦可见‘鬼子’妖魔化后所具有的人格杀伤力”⑦。抗日战争以后,“鬼子”就专指日本侵略者,而欧美国家由于援助中国抗日,中国人渐渐不再称呼他们为“鬼子 ”,偶有使用“洋鬼子”,也不带有贬义。“鬼子”一词承载着民族创伤记忆,它在不同历史时期的语义变化也体现出文化记忆“重构性”的特征。
叶兆言的《日本鬼子来了》是三个故事的拼贴,一个是作家方之的故事;
一个是日本侵华时期外婆家村上的故事,还有一个是“我”道听途说的故事,三个故事由“日本鬼子”这个词汇巧妙地关联了起来,然而在三个故事中“日本鬼子”一词的情感色彩是不同的。小说文本中作家方之所说的“乖乖,真是日本鬼子来了”,中的“日本鬼子”完全没有了贬义情感,只是一种戏谑性修辞:“这下好了,说是日本人要来了,乖乖,一个个屁颠颠,忙得鼻青脸肿。活见妈妈的鬼!”小说文本中作家方之明显是在讽刺那些崇洋媚外的基层干部。
新历史主义小说在形式上仍延续先锋文学的一些叙事特征,比如《日本鬼子来了》的文本中作者就使用了自己认识的作家方之的姓名,“方之”在小说文本中也是一位叙事者,其功能不仅在于形成一个有趣的“叙述圈套”,而且也暗示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的开始,方之直到1978 年才结束了在洪泽县的劳动调回南京市文联工作。20 世纪70 年代初中日恢复邦交正常化,一直到20世纪90 年代初,中日双边关系恢复到了战后最好状态,堪称蜜月期,在这样的变化面前,中国曾经受到日本侵略的国族创伤记忆必然会受到压抑,然而对一些个体而言,创伤记忆很难消退。
《日本鬼子来了》文本中作者拼贴的第二个故事透过白毛阿四和阿庆嫂的身体受创书写了两段国族创伤记忆。叶兆言反复描写白毛阿四身体的受虐:
那是把极短的小刀子,和我们今天的水果刀相仿佛,面目极凶的日本兵用它在白毛阿四身上扎来扎去,其目的似乎并不是想杀人,纯粹是一种发泄,一种带有游戏性质的恶作剧。
白毛阿四身子中间那一截早已血迹斑斑,咬着牙不吭声,再次忍受暴力。面目极凶的小日本仿佛面对一个没有生命的面粉口袋,拳打脚踢全无反应,于是索性站在白毛阿四身上,用劲蹬,蹲下去,站起来,蹲下去。
白毛阿四的身体受虐书写,是日本侵华战争带来国族创伤的隐喻。而另一位受创者形象阿庆嫂则是中华民族在侵略战争中受屈辱的象征。“阿庆嫂”本是20 世纪60 年代末期革命现代样板戏《沙家浜》中的艺术形象,戏中最精彩的唱段《智斗》中反派角色刁德一有句流传很广的唱词“这个女人那不寻常”,让“阿庆嫂”成为家喻户晓的角色,且成为人们心中机智勇敢的民间抗日女英雄。叶兆言《日本鬼子来了》中外婆说起阿庆嫂的那一句“那婊子实在是有本事”,无疑是对《智斗》中唱词的戏仿,外婆接下来的话“小日本后来也叫她治得服服帖帖,叫他干什么,就乖乖地干什么”,让熟悉《沙家浜》的读者很容易会联想到那个能干泼辣的革命者“阿庆嫂”形象,然而《日本鬼子来了》中阿庆嫂由于日本鬼子的侵略所受的污辱是三重的,身体上的、民族情感的和道德上的,作者以阿庆的死撕碎了日本兵三良与阿庆嫂家相处时看似温馨的画面。叶兆言以互文的方式为《沙家浜》中的革命浪漫主义想象做了补充,阿庆嫂成为抗日战争中民间女性的象征,面对日本侵略者,那些有慧心有计谋的女子虽然有像《沙家浜》中的阿庆嫂那样成为革命英雄的,但更多的还是难逃受侮辱的命运,这也是国族记忆不能抹去的部分。
杰弗里·丘比特在《历史与记忆》指出,“创伤性经历带来了更为持久的国族分裂问题,或公共和私人回忆之间的分歧问题”⑧。《日本鬼子来了》中的第三个故事就书写了这种分歧。一位缅甸远征军的老兵,曾经的抗日英雄,战后战争创伤应激反应却如影随形,“那野兽出没的洪荒莽林里安息的鬼魂,经常在风雨交加的夜晚,悄悄拜访老人的梦境”。然而他那生活在和平年代的儿子却完全不能理会这点,他和日本商人做起了生意,造成了两代人在情感上的撕裂。这样的有着不同情感记忆的两代人如何交流,那些个人创伤经验在不同历史时期无法和变化中的集体记忆调和的个体生命如何得到医治,可能是全世界范围内有过族群创伤记忆的人们所面对的共同难题,从某种程度上说,这些难以得到心理医治的个体,恰恰是审视历史的眼睛。叶兆言以作家的敏感,从记忆的维度看到了这一点。
《一九三七年的爱情》是叶兆言的长篇代表作,发表于1996 年,应该也是国内最早以“一九三七”命题的小说文本。作者说:“一九三七年的南京不堪回首。对于南京人来说,这一年最残酷的历史,莫过于震惊中外的南京大屠杀。历史材料记载,在这场噩梦一般的浩劫中,遇难同胞超过三十五万人,发生了二万左右的强奸事件。”⑨“瓦胡号”是美国在长江定期巡逻的炮艇,船长约翰·米歇尔·希汉摘录了乔治·爱希默·菲齐的日记。摘录的日记计有7 页长,时间从1937 年12 月1 日至12月31 日。菲齐记录了恐怖时期人们遭受的苦难:屠杀、强奸、焚烧与掳掠:
星期二,14日。日军大批涌入南京城——坦克、大炮、步兵、军车,恐怖降临了。在此之后的十天中,残酷恐怖的程度与日俱增……
当晚,召开委员会议时,有消息传来,日军从安全区总部附近的一个难民营抓走的1300名男子都被枪杀了。我们知道其中有一些人当过兵,但是,那天下午一名军官向拉贝保证宽恕他们的性命。他们要做什么,现在再清楚不过了。手持刺刀枪的日本兵让这些人排列成行,约一百个人绑在一起,戴着的帽子都被强行摘下,摔到地上。藉着汽车灯光,我们看着他们被押往刑场……
星期五,12月17日。抢劫、杀人、奸淫有增无减。粗略估计,昨天晚上和白天至少有上千名妇女被强奸。一个可怜的妇女被奸达37次。日本兽兵在强奸另一名妇女时,为了阻止她五个月的婴儿啼哭,蓄意将其窒息而死……
星期一,12月20日。暴力与破坏事件毫无节制地持续着。市内整片整片的区域被有计划地焚烧。下午五时,我和史迈斯开车出去。城里最重要的商业街道太平路整条街都在熊熊的烈火之中。驱车经过时,天空散落着火星,地上遍布着余烬。再往南,见到日本兵在商店里纵火焚烧,再往前行,日本兵在往军用卡车上搬运携掠来的物品……
星期三,12月22日。今晨五点,行刑队在离我们很近的地方开枪杀人,数了一下,打了一百多枪。⑩
这些珍贵的历史资料现保存在美国国家档案馆。1937 年的南京被置于了历史上的至暗处,这一年全世界许多的新闻记者、外交官员、传教士见证了“恶之花”在南京盛开,南京见证了人性中最黑暗、最残酷的一面,如今我们能读到不少披露南京大屠杀细节的历史文献、图片、影像资料和见证文学。因为大屠杀事件,1937 年的“南京”“从一个简单的地名转变成了一个有重大历史意义的象征”⑪。“一九三七年”也成为中国乃至世界历史上一个有纪念意义的年份。
叶兆言是南京人,生于1957 年,属于南京大屠杀后的第二代人,社会在“经历了重大动荡之后,余波可能延续给‘三四代人’”。⑫叶兆言的抗日叙事既是创伤记忆“世代传递”的产物,它们自身也构成对抗日战争的“文学记忆”。叶兆言以互文的方式将自己的“文学记忆”嵌入中国抗日文化记忆的大版图中,他以《追月楼》互文《四世同堂》,以《一九三七年的爱情》致意《倾城之恋》和《围城》等,都显明了这种努力。“文化记忆依然是没法被欺骗的互文性游戏的源泉,跟它的任何互动——包括对于记忆有所怀疑的互动——结果都在不断地验证着某个文化空间的存在。”⑬然而叶兆言的抗日叙事不仅强化了中华民族抗日战争的民族创伤记忆,还在于他立足于南京,由南京作为记忆的出发点,在历史的脉络上拉伸了南京城创伤性历史记忆这一文化空间,因为他经由“一九三七年”召唤起的不仅是日本侵华大屠杀的历史记忆,还有南京这座城市在历史上的悲情记忆。南京素有悲情城市之称,“从1853 年太平军攻进这座城市开始,到1864 年城池被湘军攻陷,南京基本上一直都处于战时状态,战争和杀戮没有停止过”⑭。多年后叶兆言在《南京传》中提及南京人性格上的弱点,扼腕南京的现代化进程不止一次受到战争的阻挠,其中南京人自己也难免责任,比如,太平天国的进攻使得有钱人全部离开了南京。因而叶兆言在创伤记忆书写的过程中始终伴随着对南京人的文化反思,也由此对人性进行深入的揭示和反思,这或许可以解释缘何“表现南京大屠杀时,叶兆言采用了文字上的回避策略,但当他描写中国国民在自己的同胞身上施行暴力时,却没有表现出类似的节制。”⑮
叶兆言在创作《一九三七年的爱情》之前做了大量的史料准备工作,“我从来没有为写一篇小说,下过这样深的资料的功夫。我一次次地去图书馆看旧书,翻阅当年的旧报纸杂志,那些陈旧的东西,让人有一种走进历史的错觉”⑯。最终他完成了一个爱情故事,但这并不是叶兆言面对历史的一次走神,而是以爱情故事为隐喻,表达了对1937 年的全部理解。所有关于中国抗日、关于南京城沦陷的文化记忆,包括他阅读的历史文献、文学作品都是他在构建1937 年的南京记忆时的前文本。他在小说文本的“写在前面”中那句“故都南京像一艘装饰华丽的破船”,似乎是张爱玲“人生是一袭华丽的袍子,里面爬满了虱子”的回响,都以修辞方式发出了哀叹,“到了一九三七年,南京作为中华民国的首都已整整十年。这十年,南京成了地道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我注视着一九三七年的南京的时候,一种极其复杂的心情油然而起。我没有再现当年繁华的野心,而且所谓民国盛世的一九三七年,本身就有许多虚幻的地方”。这种虚幻感,既是作者就1937 年年底开始的大屠杀事件而言的,恐怕也是他从历朝历代南京的文化记忆中早就有的。《一九三七年的爱情》透过一种近乎极致浪漫而悲伤的爱情叙事,写尽了作者注视1937 年的南京时的欣喜与感伤,丁问渔身上浪漫和浮华交织出的气质,正是一九三七年南京的味道,他最终被流弹杀死,也是对南京命运的一种隐喻,浪漫与浮华止息于暴虐。诚如学者白睿文所言:“叶兆言可能不太懂‘被历史学家称为历史的历史’,但他却将历史的忧郁和历史的难以承受的重负留给了我们。”⑰
叶兆言以爱情书写将浪漫又伤感的情感结构植入了他对1937 年的历史记忆中,而小说文本中被评论者称为“百科全书”或“档案录”的文本,无论是否完全真实都不妨碍它们成为南京沦陷的“补正”(remediation),因为“人们对于那些已经变成记忆之场的战争、革命以及其他任何事件的了解,看来主要不是指向我们可能会谨慎地称之为‘真实事件’的东西,而是指向既存的媒介结构的标准,指向媒介文化中流传的叙事和意象”⑱。叶兆言成功将对一段爱情的虚构转化为了对一座城市的文学记忆。
作家中恐怕很少有人像叶兆言那样对南京那么情有独钟,他绝大部分小说的空间背景都是民国时期的南京,叶兆言的小说往往具有浓郁的怀旧特色,“南京似乎只有在怀旧中才有意义,在感伤中才觉得可爱”。南京素有悲情城市的称号,“没有一个古老的城市比南京更适合听亡国之音”,“亡国之音”似乎是叶兆言书写南京时挥不去的记忆,也是他抗日叙事中常常引用的文本,正如他《一九三七年的爱情》的“写在后面”中所说:“当我在写这篇小说的时候,耳边常常回着这蔡琴女士演唱的那首委婉动听的《秦淮河畔》:今夜有酒今夜醉/今夜醉在秦淮河畔/月映波底/灯照堤岸/如花美眷依栏杆/歌的歌舞的舞/声声相思为谁诉/步步爱怜为谁踱/蜜意柔情为谁流露/为谁流露/歌的歌舞的舞/朵朵樱唇为谁涂/层层脂粉为谁敷/眉语眼波为谁倾吐。这分明是一首亡国之音。商女不知亡国恨,隔江犹唱后庭花,我不知《玉树后庭花》是什么样的曲调,能把国家都唱亡了。”有关明朝遗民亡国之痛的剧本《桃花扇》也不止一次出现在叶兆言的小说中,长篇小说《很久以来》里卞家花园的朱琇心师父教几个小妓女唱的正是昆曲《桃花扇》中的《折桂令·问秦淮》,此曲写的是南京荒凉残败的景象。这些“亡国之音”和中国抗日战争中的悲剧恰似构成了一种复调,形成一种强烈的历史宿命感,当叶兆言回望1937 年日本攻陷南京的历史时,他大概会想到“历史上的南京保卫战,没有一场以胜利告终”。之所以如此,在他看来,南京人在历史中形成的文化性格难辞其咎。“三十年代的南京繁花似锦,到了一九三七年,国破家亡已到最后关头,到处都在喊着抗日救亡的口号,但是悠闲的南京人依然不紧不慢,继续吃喝玩乐醉生梦死。今日有酒今日醉的名士派头,仿佛已经渗透在南京人的民风中。”⑲
这何尝不也是对中国国民的文化性格的一种反思,叶兆言的抗日叙事的启蒙文学色彩在这一点上是明显的,新历史主义思潮并没有裹挟他走向历史虚无主义,他的文化底色还是启蒙思想,他对南京城的关注,终究还是落在了对国家命运的思考,对现代性的思考,对“人”的关怀上面。首先,我们可以从新历史主义小说的寓言性特征来更好地理解叶兆言抗日叙事中的南京记忆。南京这座城无疑是国族的象征,1927 年4 月国民党正式定都于南京,1929 年到1937 年之间中国经历了走向现代化的高度发展,“1927 年至1937 年之间,是许多在华很久的英美和各国侨民所公认的黄金十年”。当时作为首都的南京无疑是现代进程的最直接的受益者,它“在突然之间,变得漂亮了,变得繁华起来,它变得非常现代化,变得开始跟国际接轨。正是在这段历史时期,当时的南京人见证了现代都市发展的奇迹”⑳。叶兆言的抗日叙事中以历史文献、日记等跨文本形式关涉了当时国民政府大量政治、经济、文化的内容,“现代化”同样是其中的关键词。叶兆言的抗日叙事不仅透过南京书写了国族的创伤史,他也追述了现代化文明世界受到野蛮掳掠的历史事实,中国现代性叙事因日本侵华战争而出现了休止符。
实施特深井(13 000 m以深)科学钻探工程之前,建立结晶岩钻探施工必要的理论基础和构建初步的技术体系是非常必要的,只有在具备较完备的理论基础和完善的施工技术体系的前提下,才能安全、高效地完成特深井科学钻探任务。
其次,叶兆言的小说常被指认为“怀旧”,然而在面对现代性国家这样的议题上,叶兆言对那些旧时代的文化遗民其实从来没有报以任何希望。他小说中的几位遗老,朱琇心只能传授传授《桃花扇》之类的亡国之音,丁老先生在《追月楼》上的自我囚禁显然对国家的前途毫无影响,连他表明自己气节的《与弟子少荆书》也只能是一个反讽修辞。叶兆言的抗日叙事回避了民族主义的情结,更没有滑至民粹主义。他还是在现代性叙事中反思日本的侵略战争,尤其是南京大屠杀,他在揭示日本大屠杀残暴的同时也特意区分开日本侵略者和支持中国革命家的日本人民,以及尊重中国文化的日本学者。齐格蒙·鲍曼在《现代性与大屠杀》中一开始就反对把大屠杀“看做是发生在犹太人身上的事情,看做是犹太历史中的一个事件”㉑。“大屠杀只能被理解为文明无法将自然留在人身上的任何不良的、与生俱来的癖好包括在内的结果。”㉒南京大屠杀亦是野蛮获胜的表征,叶兆言将对这个问题的思考扩展为任何的暴力,包括国人对国人的暴虐都可归因于未被文明规训。
第三,叶兆言的抗日叙事几乎没有直接描写战地和战斗场景,作者关注的是战争背后文明的失序和权力虚妄。叶兆言的抗日叙事中有大量的婚恋书写,他说,“战争时期的爱情将是十分荒唐可笑的,在战争的背景下,爱情往往显得非常滑稽”㉓。《刻骨铭心》中写了很多对的婚恋关系,但里面多有不伦之恋、婚外情、虐妻,没有一段的爱情关系可以称得上是刻骨铭心的,战争让人的生命中出现许多荒诞的组合。冯焕庭和丽君第一次约会下的馆子是马祥兴,然而他们并不是为了美食,也并非为了恋爱,而是为要看枪毙人。战争背景之下,很多的荒唐事件成为日常。《很久以来》开篇以12 岁的孩子欣慰的视角扫视着新街口广场:
先说新街口广场上的纪念活动,在抗战前,这里还算不上太热闹,还不是什么市中心。当时为了表示抗战决心,广场中央放置了一个巨型的炸弹模型,向南京市民提示可能来临的战争威胁。日本人真来了,具有抗日意味的炸弹模型自然不复存在,取而代之竖立在广场中央的那玩意儿有点儿不伦不类,又像纪念碑,又像广告牌,自上而下地写着一连串大字:“汪**是带领我们和平建国的领袖。”“还都周年”纪念活动的具体形式,就是聚集在广场上收听汪精卫的广播讲话。
——叶兆言《很久以来》,《收获》2014年第1期。
1941 年的3 月30 日,抗日战争还在激烈地持续中。然而1940 年,汪精卫投靠日本人,在日本的扶持下在南京建立了汪伪国民政府,汪精卫任该政权的代**兼行政院院长。但这里却呈现出巴赫金所说的狂欢,“巨型的炸弹模型”被“政治口号”取代,领袖的声音在广场传播,但领袖却是缺席的。狂欢的广场上只有排演过的中学生队伍和航校的帅小伙。作者描写出的南京市中心新街口的场面浮华而虚假,构成对发生在南京的这场政治丑剧的极大讽刺。
《很久以来》小说文本的历史寓言性特征在小说的开头得到生动的表达。就在这个“还都周年”纪念日,汪伪政府要员的司机老王把小汽车停在了新街口广场的路边,来到新街口广场东南角的现代化公厕,厕所外面,广播里的汪精卫还在继续演讲,老王“从报纸上随手撕下了一大块,上面正好还印着汪精卫的头像,老王盯着那张有些模糊的头像看了一会儿,便将报纸窝成一团,在手掌中反复来回轻揉。那年头,生活很节俭,用旧报纸擦屁股是十分常见的事情,报纸有些光滑,必须揉一揉才好使”。司机老王以近乎行为艺术的方式宣告了汪精卫的遗臭万年。有趣的是,报纸是传播文化记忆的重要媒介,在叶兆言书写的这一细节中,记忆背后的权力运作以及其必然带有的意识形态性昭然若揭。
20 世纪90 年代以后,由于国内一些新历史主义小说出现了消费历史、游戏化历史的倾向,新历史主义小说中的历史虚无主义倾向受到批评,中国当代文学中的新历史主义思潮也随之消退,叶兆言是少数的新历史主义小说创作的坚守者,而且以创作实绩表明一个新历史主义小说家同样可以追求做到“小说不是历史,然而有时候,小说就是历史,比历史课本更真实”㉔。这也让我想到新历史主义者曾有言:“在任何文化中都存在一个普遍的象征体系,它由无数能够激起人们的欲望、恐惧和敌意的符号组成。因为文学艺术家‘能够建构引人共鸣的故事,可以有效把握意象,尤其是他们对语言这一文化最伟大的集体创作非常敏感,所以他们擅长操纵这个象征系统。”㉕我认为从记忆理论这个角度,我们完全可以对新历史主义小说有一些积极的期待。
【注释】
①叶兆言: 《一九三七年的爱情·写在前面》,江苏文艺出版社1996 年版,第5 页。
②㉕赵一凡等主编:《西方文论关键词》(第一卷),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17 年版,第673 页、673 页。
③赵静蓉:《文化记忆与身份认同》,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5 年版,第59 页。
④⑤曹翔:《“鬼子”释义考辨》,《语言研究》2007 年第4 期。
⑥这方面研究可见谢丹、黄迎新:《 从“鬼子”称呼看晚清的中西文化交流》,《湖北社会科学》2006 年第3期;
许龙波:《从“鬼子”词义及其指称变化看近代中国的外来侵略者》,《全球史评论》2021 年第1 辑。
⑦许龙波:《从 “鬼子”词义及其指称变化看近代中国的外来侵略者》,《全球史评论》2021 年第1 辑。
⑧ [英]杰弗里·丘比特:《历史与记忆》,王晨凤译,译林出版社2021 年版,第225 页。
⑨叶兆言:《一九三七年的爱情·写在后面》,人民文学出版社2017 年版,第362 页。
⑩[美]陆束屏编译:《历史上的黑暗一页:英国外交文件与英美海军档案中的南京大屠杀》,江苏人民出版社2017 年版,第29-30 页。
⑪[丹麦]何铭生:《南京:1937·前言》,季大方等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7 年版,第8 页。
⑫⑬⑱ [德]阿斯特莉特·埃尔、安斯加尔·纽宁主编:《文化记忆研究指南》,李恭忠、李霞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21 年版,第154 页、377 页、488 页。
⑭叶兆言:《南京传》,译林出版社2019 年版,第413 页。
⑮⑰ [美]白睿文:《罗曼史下的暴行:叶兆言的〈一九三七年的爱情〉》,潘华琴译,《南方文坛》2016 年第6 期。
⑯⑲㉓叶兆言:《一九三七年的爱情》,人民文学出版社2017 年版,第363-364 页、69 页、364 页。
⑳ 叶兆言:《南京传》,译林出版社2019 年版,第479 页。
㉑㉒[英]齐格蒙·鲍曼:《现代性与大屠杀》,杨渝东、史建华译,译林出版社2011 年版,第1 页、17 页。
㉔叶兆言:《一号命令·后记》,江苏文艺出版社 2013 年版,第154 页。
猜你喜欢叶兆言鬼子南京“南京不会忘记”环球时报(2022-08-16)2022-08-16南京大闯关儿童故事画报(2020年8期)2020-10-30秦淮河畔、古城墙下,叶兆言《南京传》南京首发阅读(书香天地)(2020年2期)2020-04-07万国造枪打鬼子小哥白尼(军事科学)(2019年8期)2019-11-16叶兆言教子:“学无先后,达者为师”黄河黄土黄种人(2019年5期)2019-07-17牛山魁打鬼子文学少年(原创儿童文学)(2019年4期)2019-05-23艰难的行走(随笔)作品(2018年9期)2018-09-10南京:诚实书店开张新高考·英语进阶(高二高三)(2016年1期)2016-03-05南京、南京连环画报(2015年8期)2015-12-04叶兆言:无意中走进雷区小康(2010年6期)2010-02-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