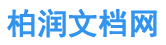邱心玫,张荣伟
(福建师范大学教育学院,福建 福州 350007)
教育术语是凝聚着教育学知识的关键词,就其本质而言是教育概念系统的语言符号。教育术语首先是一种语言符号,可以是一个词、一个短语,或是一个词、一个短语与特殊符号的组合等;
其次,它与教育领域所使用的规范相对应,表达了教育领域的特殊概念,用以解释、说明某种教育对象、教育行为、教育理念或教育制度。
多年来,在国家的大力支持下,以《教育学名词》《大辞海(教育卷)》《教育大辞典》为代表的,经由学术共同体审定通过的教育学术语相继公布、出版;
陈桂生教授的《常用教育概念辨析》[1]、项贤明教授的《论教育学的术语和概念体系》[2]、石中英教授的《教育学研究中的概念分析》[3]、孙绵涛教授的《教育范畴论》[4]等著作和论文,也就教育术语、教育概念等问题展开广泛讨论,为教育术语的研究和规范奠定了一定的基础,但这些成果并未形成一套明确、完整的术语体系。截至2022年6月26日,在中国知网上以“教育术语”“教学术语”“教育概念”“教育范畴”为关键词,搜索到相关文献共计148篇,主要都是围绕对教育术语、教育概念的审思和辨析,鲜少涉及教育术语的本质分析和体系构建。与此同时,教育研究和教育实践中的教育术语失范现象屡见不鲜,亟待教育工作者和社会各界予以重视并协同解决。
相关教育文献和教学实践的术语分析结果表明,由于使用者的教育术语意识淡薄或缺失,导致教育概念、教育术语在教学、研究和传播中的失范问题层出不穷。
(一)教育术语表达层面准确度的缺失
当前,无论是在日常教育,还是在学术研究,甚至是在教育政策中,都常常出现教育术语表达不准确的现象。诸如“德育教育”“智育教育”“体育教育”“美育教育”等富有争议的词语屡见不鲜。《大辞海(教育卷)》指出:“德育是思想教育、政治教育、道德教育等的统称”[5]13;
“智育为促使人的理智发展的教育”[5]3;
“体育即身体的教育,指通过身体运动或游戏促进个体心因动作技能发展的活动”[5]3;
“美育亦称审美教育,是关于审美与创造美的教育”[5]4。不难发现,“德育”“智育”“体育”“美育”皆为偏正结构,且已含有“教育”之义,在其后再添“教育”二字不仅画蛇添足,语义逻辑搭配并不当。[6]又如“应试教育”一词,常被指称“有考试的教育”,扭曲了考试作为教育评价手段的中立性。在具有广泛群众基础的教育领域,“教育”“教学”“素养”等教育术语容易被人们在不加界定或全凭直觉理解的情况下随意表达,颇有将教育术语转化为日常用语之势,从而模糊了教育工作者对日常教育经验和科学理论边界的认识,阻碍了教育术语的规范化应用,妨碍了教育工作者对教育现象、教育概念和教育术语体系的正确梳理和关系构建。
(二)教育术语理解层面语义泛化严重
在理解教育术语的过程中,语义泛化的问题突显,主要表现为最初的语义不断减弱,其所反映的教育概念外延不断扩大,使用范围和用法急剧增加。目前单是“课程”的概念已多达上百种,而诸如“生命教育”“幸福教育”等较为抽象且涉及情感、价值的术语,常常伴随着语义泛化的解读和个体赋义。又如具有三重意义指向的儿童哲学(即关于儿童的哲学、属于儿童的哲学、为了儿童的哲学)[7],在教育理论研究中常常与一般意义上的儿童哲学教育以及马修·李普曼创立的儿童哲学教育(项目)相混淆。如上种种容易导致概念本质属性的消解和教育概念发展、创生的随意性,加剧教育理论研究和实践研究的困难,以及教育研究者和教育实践者之间的对话障碍。
(三)教育术语生成层面丛林现状凸显
随着新一轮教育改革的推进,一线教育工作者通过叙事研究、行动研究、校本研究等研究方法实现教育研究者的教师角色塑造,在促进教育实践改革和丰富教育教学理念的同时,也产生了“教育概念的丛林”,诸如“雅文化”“石文化”“菊花课程”“荷花课程”等教育概念层见叠出。正如石中英教授所言,有些学校在学校管理、教育教学上硬是先行制造或拿一个看起来、听起来很新颖的概念,也不管它科学不科学,明确不明确,就把活生生的学校管理和教育教学实践塞在这个概念下面,实为削足适履、作茧自缚。[8]审视教育概念丛林现状背后的术语逻辑,不难发现上述形形色色体现某种教育主张的教育概念是中小学特定校本改革的派生概念,并通过合成词的构词规则,形成貌似标准且富有学术意义的名词。继而,五花八门的教育概念,借由其语词形式,形成了“教育术语的丛林”。然而,教育术语丛林中许多点状分布的所谓“教育术语”,实则流于术语的外部形式,其语义(内部形式)却难以涵盖承载对象(即此概念所对应的对象)的性质特征,所指称的概念也缺乏理论基础和方法论指导,与教育原理和教育哲学理论体系不可通约,须基于实践沉淀进一步提升其解释力和指导力,方能形成教育知识网络上的节点,最终融入理论化、规范化、系统化的教育术语体系。
(四)教育术语交流层面盛行“拿来主义”
在教育学科发展和国际交流的过程中,教育术语的“拿来主义”具体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一是学科间的“拿来主义”。从教育学形成之初,教育术语就逐渐出现引鉴或直接运用其他学科术语的状况。二是语际间的“拿来主义”。我国教育研究领域常出现“一旦捕捉到西方教育界冒出的什么新名目、新流派、新设想,既迫不及待地趋之若鹜,又很快随之销声匿迹,而更换的新名目、新流派、新设想”[9]的现象。教育术语的“拿来主义”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教育学科特色和元研究的结果,容易忽略中西方教育研究的文化差异,从而导致教育术语结构体系难以自洽,产生语义漂移,甚至割裂教育概念、教育命题、教育理论和教育哲学方法论之间的关联,不利于中国特色的教育话语和教育术语体系的建构。
上述教育术语失范现象受到教育领域内外各方因素的影响,就术语学视角而言,可从如下几个方面进行审视和追因。
(一)教育学科源头的术语错觉
探究教育术语失范问题的深层原因,可追溯到现代教育学构建之初的术语构成与发展。现代教育学的基本概念和教育术语大都是以古代拉丁语或希腊语中某些语词为词根建构的新词,有别于日常用语,体现了教育学科的逻辑起点、文化源流和价值取向。然而,伴随着教育学引入我国,对西方教育术语的翻译出现了原义与汉语语义的混淆和杂糅、一词多义、原意转义跨度大等情况,陈桂生先生形象地将此类现象称为“西学东渐的错觉”[10]。此外,在汉语词汇双音化发展的过程中,在保持原有单音形式语义的基础上,逐渐通过双音并列的形式,形成音步,构成韵律词,创造双音词。[11]而以双音词形式呈现的、西方引入的现代教育术语,与以单音词形式呈现的、传统的、沿用至今的教育术语,存在内涵、外延或语义突变,却在教育领域给人带来“本应如此”的错觉。
(二)术语学和术语教育的教育学缺位
术语学研究始于20世纪30年代,主要关注术语与术语体系的逻辑问题,注重概念的本质、特征和定义,概念间的关系,术语标准化的实际问题,并逐渐从综合性科学变成了由相关学科组成的综合体。在教育领域中,虽然已有教育学名词释义以及隐性的、零星的教育概念和术语研究,以及较早开设的“教育术语学”研究生课程探索(如福建师范大学),但是在术语学的科学体系中,教育学尚处于缺位状态。与教育术语学相适应的师范生教育类术语课程尚未独立开展,严重阻碍了教育学整体的科学化发展和教师队伍的专业化建设。教育术语的统一和规范化之所以没有达到应有的水平,根源就在于教育术语学的学科缺位。因此,中国特色教育术语学的初步构建与实践探索就显得十分迫切。
(三)教育术语生成的周期制约
术语学的研究表明,规范的、完备的、符合科学标准的术语系统并不天然伴随学科的产生而发展完善,形成科学术语前可能经历原始术语、初术语和准术语3个阶段,教育术语学的形成亦是如此。[12]教育科学产生前已经出现可以用来指称教育术语承载对象的词汇单位——原始术语,它们大多被保留在流传至今的传统教育活动和日常词汇中。而那些暂时找不出合适术语对应、呈现出临时性、不稳定性非普遍接受性的教育新概念或专业词,被称为初术语。它们大概率会被更符合术语特征的教育词汇所取代,也有可能在长期使用中获得稳定的性质而发展成为准术语。伴随着教育科学化的进程,教育理论与实践工作者们对教育现象和教育问题的认识会上升到理论性的高度,与理论性认识相适应的名词一经进入教育科学概念系统,便可能进入教育专业语言之列,并最终成为科学的教育术语。由此可见,科学教育术语的形成需要经过一定的术语生成周期。当前教育理论探索和实践变革中所呈现出的不同解释力的“术语丛林”现状,实则为处于初术语、准术语和科学术语三大发展阶段的教育术语竞相展示、混合杂糅的存在样态,有待进一步厘清和系统化,以实现理论升华,获得学习共同体的认同。
教育术语系统是国家社会科学术语体系的—个重要部分。从教育科学化视角审视,对教育学科体系内的名词术语进行审定和规范,是教育学科繁荣发展的具体标志之一。全国科学技术名词审定委员会于2006年便将教育学名词审定工作放到了突出位置,并把这项工作委托给教育部,以推动教育事业的发展、教育科研的开展、国际教育交流与合作等。[13]作为教育术语编撰成果,《教育学名词》和《大辞海(教育卷)》分别体现了推广规范教育术语的两种常见模式,前者是以颁布国家标准的形式,后者是以编纂辞书的形式,二者皆为教育术语工作实践提供了基础性的规范。前期的教育术语规范化工作虽然大大促进了教育学科发展的进程,但却并不意味着可以直接实现教育术语的自觉规范化。因此,教育界应进一步加强教育术语的规范化建设。
(一)顶层设计:完善教育术语规范机制
1.健全教育术语规范的宏微观机制
为进一步推进教育术语的规范化建设,加强教育行政部门、术语组织与各级各类学校的协同合作,完善教育术语规范的宏观与微观机制。首先,在宏观层面上须进一步加强教育行政部门与术语组织对于教育术语的规范化协同。在建立教育术语审定机构的基础上,积极开展教育术语的收集、分类、鉴别、选择等工作,将教育术语编辑成册,定期修订,再通过国家授权公布以成为社会定约,并逐渐形成教育术语规范的“行政机制”(即制度化流程与规范),不断完善教育术语规范的宏观机制主体。[14]其次,在微观层面上须进一步补齐教育术语规范的“基层”短板。在教育行政部门和国家术语机构的领导下,建立健全教育术语规范的“学校机制”,提升各级各类学校领导者的术语管理能力;
加强原有学校学术机构的术语研究和术语规范功能,唤醒广大教师的教育术语规范意识,培养其教育术语能力,规范其教育术语运用。
2.形成教育术语规范的双向通道
结合教育政策、教育研究和语言规范分类的相关理论,基于国内外教育改革和术语规范的发展规律,教育术语规范应从“自觉的规范”和“自发的规范”两方面入手,探索教育术语规范的双向通道。
一方面,从“自觉的规范”视角入手,理顺教育术语规范自上而下的通道。教育术语自觉的规范包含由国家机关、教育行政部门、教育术语机构、专家和学校参与,旨在统一与规范教育语言、消除语言差异标准语的教育术语审定、编撰、推广、实践等一系列活动。在教育术语规范实践中,应加大教育行政部门和国家术语机构的组织与支持力度,注重以高校为主的教育术语主流研究,开展以师范院校为主的教育术语实践,推动各级各类师范生的术语教育与学习,发展大中小幼教师教育与培训,继而覆盖大中小幼全教育领域的教育术语与教育用语的规范化,形成自上而下的势能。
另一方面,从“自发的规范”视角入手,打通教育术语规范自下而上的通道。为保持教育过程、教育理念交流的一致性,教育主体习得教育术语的过程,应带有一定的自发性,可视为教育术语“自发的规范”。在教育术语规范实践中,不能忽视基层教育术语方面零碎的、局部的、自发的规范实践,应采用规范化管理机制,打通向上通道。具体而言,可通过教育实践领域用语的规范与创新,倒逼高校教育理论研究与师范教育实践的规范与创新,呼唤教育行政部门、新闻传媒主管部门、国家术语机构出台并调整政策,形成自下而上的动能。
如此反复,上下双向通道形成闭环,相辅相成。教育术语规范的双向通道也符合我国著名语言文字学家周有光先生关于“科技术语双语言”“双层制度”的底层逻辑设计,有利于教育术语规范化。简言之,只有国家机关、教育行政部门与术语机构通力合作,进行顶层设计和教育政策制定,再协同学校、传媒等多方力量,才能促进教育术语的规范化发展。
(二)学科建设:夯实教育术语规范的学理基础
1.找准定位,明确教育术语学的学科属性
要开展教育术语学研究,首先应对教育术语学进行科学定位。基于客观世界、思维世界和符号世界“三个世界”的逻辑关系,作为一种教育语言符号,教育术语兼备指示教育现象名称和反映教育概念内涵的功能,教育术语和所指称的教育概念呈现着对应关系。任何一门基础性质的学科,只有形成本学科的专门概念,并且尽可能严格地保持自身的基本概念,进而培植出本学科独立的见识,作为研究范围的核心,才可能在林立的基础学科群中具有独立设置的价值。[10]建构系统的教育术语体系,厘清教育学的概念及其关系(如属种关系、联合关系等),有利于揭示教育学一级学科、二级学科领域以及教育实践领域中概念与概念间的逻辑渊源和结构关系。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教育术语一方面指称教育专业知识领域内的概念,是教育理论体系的基石;
另一方面,它又可以从术语视角对教育学自身的理论陈述和研究状况进行审视和探究,从而提升教育主体的术语自觉和理论自觉,促进教育学的发展。作为研究教育术语的一门学问,教育术语学可定位为构建元教育学研究领域的综合性学科;
而作为元教育学的教育术语学,应主要研究教育领域的概念及其语言表达,融合教育学、术语学、逻辑学、语言学、信息科学等多学科知识为一体,体现学科的综合性特点。
2.特色发展,探寻教育术语学的中国智慧
随着教育国际交流的普遍化和常态化发展,国内外教育领域的理论和实践交流互动日趋密切,教育术语与教育概念的互鉴与交融诉求不断增强。教育术语学建设也必须植根于中华文化的沃土之上,为国际教育术语发展提供中国智慧。首先,明晰教育术语的中华文明根基。在使用教育术语的过程中,必然会受到传承它的语言文化的影响。作为中华文明重要象征的汉字,以形表义的特点远超其表音性质。明确汉语词源和字源(包括汉字的音义关系、形义关系、造词特点),并基于此梳理和解析教育术语的原意、转义和现代释义的产生与发展,是挖掘教育术语文化性功能的重要手段。而在术语翻译时,也应注重在领会教育概念本质的基础上,结合汉语系特点和本民族语言文字的使用习惯,进行教育术语语际转化。其次,探索中国特色的教育术语学科建设。在吸收借鉴国际术语学理论和教育术语实践经验时,应结合中国教育的沿革规律,探索具有中国特色的教育术语学,进行相应的教育术语科学研究、课程建设、教材建设、学科梯队建设,并开展体现文化自信和适合中国话语体系的教育术语教育。
(三)术语教育:增添教育术语规范的实践抓手
开展面向教师和师范生的教育术语教育,即增添教育术语规范的实践抓手。加强以培养教育术语意识为中心、规范教育术语行为为导向的师范教育与教师培训,注重课程内容、教学方法、术语训练和管理平台等方面的构建,探索“全教学对象”(覆盖各级各类师范生、教育相关专业本科生与研究生、大中小幼在职教师等)、 “全要素体系”(涵盖教育术语的定义、特点、构成、类型、语义、命名、审定、规范、翻译、管理等)、“多方教育渠道”(依靠学校课堂、教育培训和大众媒介)、“多元教学方法”(提倡教育术语系统化专题讲授、教育术语案例教学、项目教学、计算机辅助教学等)的教育术语培育范式。此外,大中小幼校长也应加强教育术语意识,注重学校教育术语管理,提升术语管理能力。一言以蔽之,作为教育术语规范实践抓手的术语教育,应以师范生术语教育和教师岗位术语培育为主要切入点,强化教育术语知识传授、教育术语意识培养、教育术语能力锻造、教育术语规范塑造,继而撬动大中小幼教育术语教学变革和教育领域的规范化建设。
猜你喜欢教育学术语概念——《教育学原理研究》评介">究教育学之理,解教育学之惑——《教育学原理研究》评介高教发展与评估(2022年6期)2022-12-09实践—反思教育学文丛中国德育(2022年10期)2022-06-20Birdie Cup Coffee丰盛里概念店现代装饰(2022年1期)2022-04-19幾樣概念店现代装饰(2020年2期)2020-03-03学习集合概念『四步走』中学生数理化·高一版(2018年9期)2018-10-09韦钰:神经教育学与创新力培养商周刊(2018年15期)2018-07-27聚焦集合的概念及应用中学生数理化·高一版(2017年9期)2017-12-19对我国音乐教育学 学科建设的一些思考中国音乐教育(2014年3期)2014-05-16有感于几个术语的定名与应用中国科技术语(2012年3期)2012-03-20从术语学基本模型的演变看术语学的发展趋势中国科技术语(2012年3期)2012-03-20